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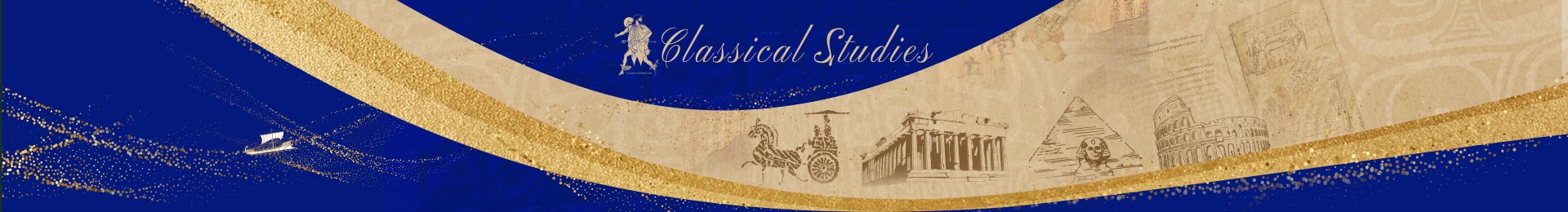
2025年3月26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古典学研究前沿”系列讲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133会议室正式拉开帷幕。首场讲座以“西利和波考克论英帝国秩序图景”为主题,主讲人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的张帅老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清露老师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嘉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姚啸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政治哲学所的贺晴川等三位老师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本次讲座吸引了线上线下众多学者和学生的积极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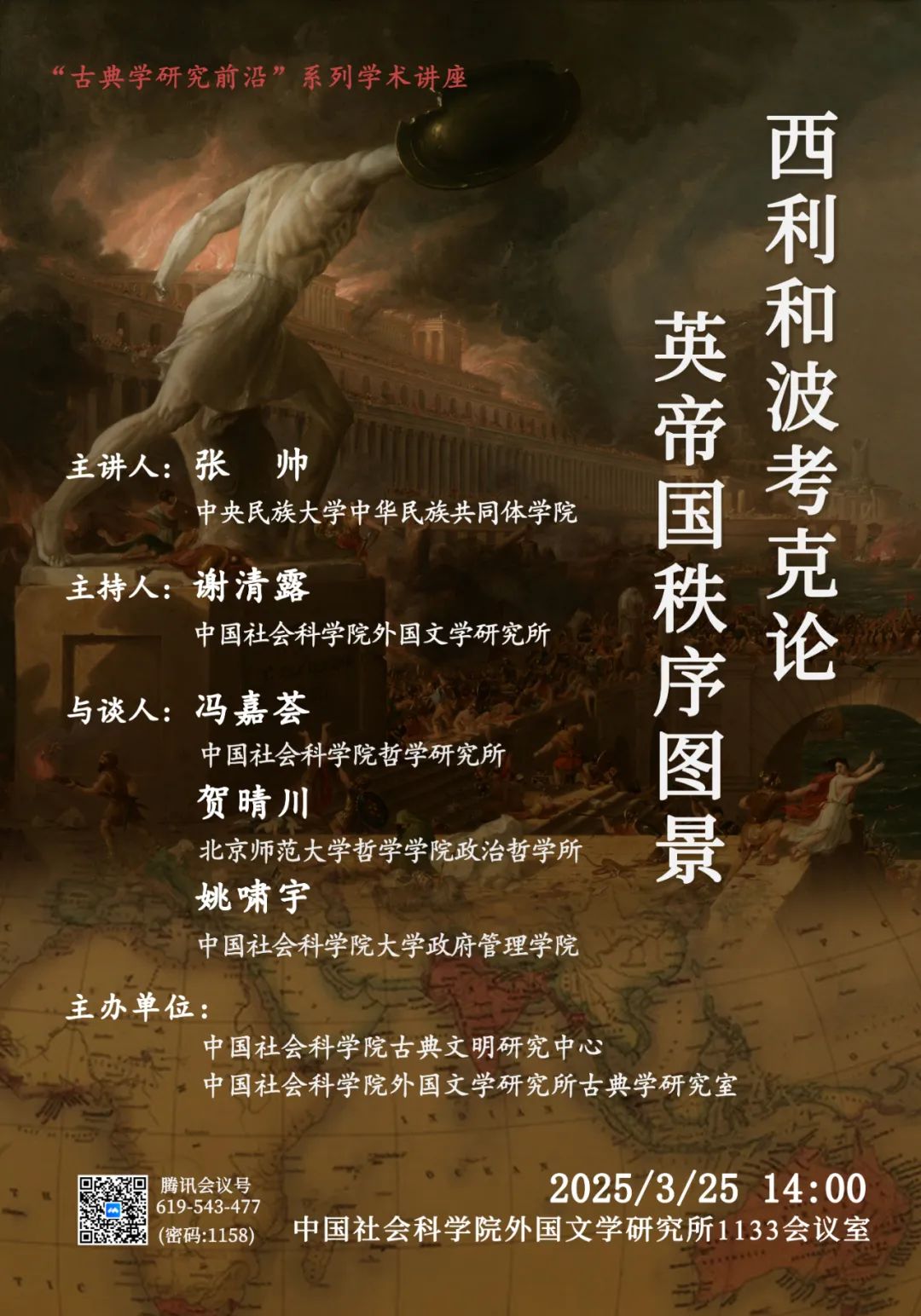
张帅老师以政治哲学中帝国研究的缺失作为开场。他指出,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长期以古代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而帝国问题往往被边缘化。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围绕城邦展开,将政治统治与帝国统治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区分了政治统治(politikon)与专制统治(despotikon),这种二分法成为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预设。思想史学者阿米蒂奇(Armitage)曾提出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就其定义本身而言,所谓的政治思想就是城邦(polis)的历史。”这意味着政治哲学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城邦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民族国家时代进一步强化,完全遮蔽了帝国史的写作。

▲ 主讲人张帅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张帅老师转向了古希腊史学传统。在希罗多德的《原史》中,对帝国兴衰的观察贯穿全书,然而,这种对帝国命运的思考从未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的描述则更为复杂,他通过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展现了帝国的荣耀,雅典展现了帝国的脆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那句著名的话:“获取这个帝国是不正义的,而现在放弃它则是不明智的。”这句话揭示了帝国统治的根本困境——建立时的不义与维持时的必要之间的张力。
进入现代政治哲学后,帝国问题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张帅老师引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休谟的观点指出,无论是古代城邦还是现代国家,之所以成为政治哲学标准叙事的核心,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人类努力可以塑造的领域,而国际关系和帝国扩张则被视为充满偶然性的领域。这种区分使得帝国问题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哲学的主流讨论之外。然而,晚近以来帝国研究的复兴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战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促使学界反思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二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凸显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帝国主题并未消失。这些变化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帝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角色。
讲座的第二部分聚焦19世纪历史学家西利对英帝国的研究。西利的“英格兰的扩张”课程在1883年结集出版,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英帝国本质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主要由广泛散布在全球的单一民族形成的普通国家”。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英格兰扩张历程的独特解读上。西利将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视为现代英帝国的起点,认为从那时起,这个位于欧洲西北边陲的岛国开始通过海军力量和商业网络向外扩张。与古希腊殖民活动不同,英国的海外扩张是国家支持的系统性工程,移民们“带着自己的国家一起”迁移。
西利特别强调英帝国与其他欧洲帝国的区别。他认为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外交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自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就将自己定位为“欧洲政治的离岸平衡手”,避免直接参与欧洲大陆争霸,同时维持欧洲均势。这种战略使英国能够将资源集中用于海外扩张,而西班牙和法国则因同时追求欧洲霸权与新世界扩张而耗尽国力。西利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观点:英帝国的扩张对暴力依赖较少,因为它主要由同一种族的国民组成。他以北美殖民地为案例,认为当地印第安部落发展程度较低、人口密度较小,使得英国人能够以较少暴力实现殖民。这种观点显然受到洛克劳动产权理论的影响,将殖民地的建立视为通过劳动获取土地的合法过程。
然而,张帅老师也指出西利的分析存在严重缺陷。最明显的是他对北美殖民地独立(1776年)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西利认为这是黑格尔原则的一次完美展现,是自由原则在更广阔领土上的实现,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将独立归因于偶然的宗教因素,认为英国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这种解释的苍白暴露了西利英格兰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他无法真正理解殖民地视角下的帝国经验。此外,西利的框架难以处理爱尔兰、苏格兰等地区的复杂角色,也无法解释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的特殊性。有学者批评西利的观点过于“美国化”,将英帝国简单地类比为美国的西进运动。

▲ 讲座现场
讲座的第三部分转向20世纪政治思想史家波考克对英帝国的重新诠释。波考克在1973年的著名演讲《不列颠史:为一个新学科的申辩》中,对西利的单一叙事提出了根本性质疑。他批评传统不列颠史要么是以英格兰史为核心加入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为佐料,要么是用英格兰史代替不列颠史,这两种模式都忽视了帝国内部的多元互动。波考克主张,真正的不列颠史应该处理盎格鲁-凯尔特边界上的“一组文化(形成的)复数历史(the plural history of a group of cultures)”。
波考克将不列颠史分为三个阶段来展现这种复杂性:第一阶段(5—13世纪)是诺曼征服后核心政治区的形成与扩张;第二阶段(1453—1688年)是英格兰退出欧洲大陆后的内部整合,特别是17世纪“三个王国的混战”(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第三阶段(1688—1815年)是英国参与欧洲争霸同时向大西洋扩张的时期。通过这种分期,波考克展现了不列颠秩序如何通过复杂的权力架构将不同地区纳入统治。例如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1801年不列颠与爱尔兰的联合,都不是简单的同化过程,而是形成了“帝国性的国家”——表面上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包含着多重主权。
张帅老师特别分析了波考克对美洲革命(1776年)的解读。与西利不同,波考克认为这是不列颠第一帝国体制的瓦解,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光荣革命后建立的“王在议会”体制本质上是寡头财阀制度,而美洲殖民地作为“没有宫廷的乡村”,无法参与议会政治,这成为独立的根本动力。英国最终选择以最低代价放弃美洲,这种“以不深切挂怀的方式丧失一个帝国”的态度成为后来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模式。波考克指出,英国与罗马的根本区别在于:罗马让帝国吞噬了自己,而英国则通过保持本土政治秩序的稳定性避免了这一命运。
在评价波考克的贡献时,张帅老师认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推进了帝国研究:一是以“政治体扩张”取代“英格兰扩张”,建立了更复杂的分析框架;二是深化了对美洲独立影响的理解;三是揭示了历史写作与政治主权的关联。然而,波考克的“保守自由主义”立场也存在内在矛盾:他既主张多中心视角,又强调不列颠政治传统的重要性;既批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去政治化”,又难以解释后帝国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张帅老师最后引用波考克的比喻:不列颠文明如同一个冷却中的星系,其他星座需要建立自己的宇宙学。这个浪漫化的愿景恰恰忽视了坚实的制度力量在帝国运作中的作用。

▲ 讲座现场
在与谈环节,冯嘉荟老师基于政治思想的力量、合法性与法律制度三个维度,提出帝国研究面临的根本困境在于如何确立规范性基础。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合法性概念很难直接应用于帝国分析,因为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冯老师特别质疑波考克理论中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强调多中心互动,另一方面又主张回归主权核心,这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她以法国北非移民的认同困境为例,说明后殖民时代的身份政治远比理论设想更为复杂。
姚啸宇老师的评论则着眼于思想史的脉络。他将英帝国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考察,指出哈耶克对英国“自发秩序”的赞美与帝国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姚老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英帝国独特的间接统治模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社会的“末人化”倾向?他引用施密特对“去政治化”的批判,提醒我们注意帝国秩序中隐藏的象征性暴力。
贺晴川老师的发言聚焦于古今帝国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古典帝国理论强调统治者的德性修为,如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帝国因骄傲自满而衰落;现代帝国则依靠制度化的权力运作,这种转变反映了政治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贺老师认为,波考克提出的“保守自由主义”存在着疑难:是要保守某一传统,还是要采取某一灵活的保守姿态?这个平衡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

▲ 评议与讨论
在自由讨论阶段,听众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有听众问及古今帝国的本质区别,张帅老师回应说,现代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将经济权力与军事力量系统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可持续的扩张机制。但这种现代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特别是文明等级论的隐性延续。另一位听众就英帝国认同建构提问,张帅老师指出,西利代表的是一种进步史观,将帝国视为文明传播的载体;而波考克则更关注认同建构中的权力因素,强调历史叙述的政治性。
讲座最后,张帅老师总结了帝国研究的当代意义。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帝国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国际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平等。虽然殖民帝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帝国思维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持久的知识、权力不对等等方面。要突破这种困境,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是要真正通过智识上的努力去克服。
本次讲座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现场讨论热烈而深入。通过分析西利与波考克两种理论范式的对话,听众对帝国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主持人总结时所说,帝国研究不仅关乎历史理解,更与当代世界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

▲ 合影留念




